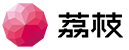發(fā)現(xiàn)打開電影dive into movie《燃燒》:充滿謎團(tuán)的世界

介紹:
李滄東在《燃燒》中表現(xiàn)出一個更為精致與成熟的自己,他一反沿之前在《詩》中外部與疏離的拍法,而與強(qiáng)大的文本相結(jié)合,完全從個人帶入,使得《燃燒》的體驗(yàn)更為極致,直接演化為一種世界的“謎團(tuán)感”。故事中的鐘秀好似被“現(xiàn)象學(xué)”般地拋到這個世界里,李滄東優(yōu)秀地捕捉了當(dāng)他面對這個世界時那充滿迷惑反映與狀態(tài),并將其自覺地構(gòu)造為謎團(tuán)的美學(xué)。
觀眾跟隨男主角的行動也一頭扎進(jìn)這團(tuán)迷霧中。隨著故事的推進(jìn),李滄東不僅展現(xiàn)了鐘秀所認(rèn)定的故事邏輯,還處處留有細(xì)小的“松動”,提示這團(tuán)迷霧仍有其他不同的入口,使得《燃燒》有了豐富的多義性,在效果上讓觀眾與角色一同困惑,可謂有趣且精妙的做法。
《燃燒》究竟是一團(tuán)怎樣的迷霧,影片中“似是而非”的狀態(tài)是如何構(gòu)造出來,并在感官上直接抵達(dá)觀眾的,李滄東在創(chuàng)造這個世界時運(yùn)用了哪些做法,使得這個謎團(tuán)具有美感,又同時留下了怎樣的遺憾?@電影傳送門 的線下觀影會映后討論都一一給出了答案。
大家還在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