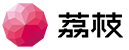發(fā)現(xiàn)大宸Radio拉薩在我的記憶里只有1980年代

介紹:
文/梁子
北京人,16歲當(dāng)兵,畢業(yè)于解放軍南京政治學(xué)院新聞系,9次獨自前往非洲,是中國首位深入非洲部落進行人文調(diào)查的女?dāng)z影師,先后在伊朗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老撾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等地拍攝紀錄片和照片,2009年11月,成為第一位進入駐阿富汗北約軍營的中國女?dāng)z影師。
“西藏是一個凈化心靈的地方,人的一生必定要去一次那里。”
自從這種說法被廣泛流傳后,我基本就沒再提過有關(guān)西藏的事。
我不知道自己1980年代去西藏,是否算做已經(jīng)被凈化過的人,當(dāng)然,還有比我更早進過藏的人們,他們都算嗎?
記得1983年,我在青海省軍區(qū)當(dāng)攝影干事,借故去格爾木采訪,有一天,偷摸著獨自跟兩個大貨車司機談好,搭著他們拉貨的車,盡管在青藏線上遭遇了車禍,我又屬于違紀行為,最終,一路坎坷地終于站在了布達拉宮前,真的被這座建筑震撼了。
那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進拉薩。
1987年5月,我從老山戰(zhàn)場下來,被部隊“強令”進了英模報告團,巡回報告過后進入秋天,我是鐵了心的想卸掉頭上那頂沉重的“英?!惫鸸?,算是順利地調(diào)入了西藏軍區(qū)政治部宣傳處工作。那時的西藏,真是一個躲避“風(fēng)頭”的好地方,冷清得幾乎無人問津。路途遙遠又偏僻,交通不便又繁瑣,水電不足又匱乏??晌揖褪菗醪蛔〉南蛲抢?,至今都無法解釋自己當(dāng)時的行為。
1987年11月, 強大的氣流把我托上了珠穆朗瑪和布達拉,思緒如天空的鳥兒自由飛翔。到西藏去的真正目的我不明晰。明朝的張岱曾寫過“西湖夢尋”,那我就來一個“高原尋夢”吧。這個夢或許就是一個緣。
那時西藏軍區(qū)所在地叫“金珠路”,占地碩大的軍區(qū)大院,不論距拉薩著名的八廓街、太陽島還是拉薩河都很近。我被組織安排住在一間鐵皮屋頂?shù)钠椒?,墻上糊著發(fā)黃的白紙,屋里有一張單人床和一張桌子。沒有爐子,也沒有煤,每周只有四個晚上供電,到凌晨12點。用水在門外,大家共同享用。
我的門前有一棵枯死的大樹,樹下搭建了兩個雞窩,右邊是垃圾坑,左邊是個用土坯壘起的公共廁所。這種條件,在當(dāng)時的拉薩市,人人也不過如此。
然而我們這些1960年代生人,盡管沒有老三屆當(dāng)年上山下鄉(xiāng)屯墾戍邊那么熱火朝天,骨子里的熱血豪情還是不減前輩的。當(dāng)時我剛從老山戰(zhàn)場上下來,對這些“不盡人意”的生活條件,似乎也不覺得多苦。
剛進藏時最不能忍受的是軍區(qū)政治部食堂,不知道糧食不夠還是炊事員偷懶,早飯稍微晚去10分鐘就沒飯了,餓到中飯?zhí)崆?0分鐘趕到食堂,還是晚了一步。周六只賣生掛面,對我這種剛?cè)サ膯紊?,哪里有爐子和燃料?好不容易挨餓到周日,食堂休息,沒飯。上街想找一家餐館吃頓便飯,絕對是難上加難,我被無數(shù)次饑餓挑起滿腹怒火,剛?cè)ツ抢镉譀]有人訴說,只能是一忍再忍,我心想,如果有一天一個女兵餓死在軍區(qū)大院里,這種新聞能往出爆嗎?誰又能知道事情的真相?
這絕對是我1987年剛進拉薩那幾天最真實的狀況。
八廓街距軍區(qū)大院僅有一條馬路之隔,那里代表了拉薩的心臟。它以大昭寺為中心,像一個順時針滾動的大羅盤。以大昭寺為起點,人們在寺院門前磕長頭,頂禮膜拜。用他們強壯的身體,伏在石鋪的地面上。之后,手持轉(zhuǎn)經(jīng)筒,撥動羅盤旋轉(zhuǎn),嘴里還不時發(fā)出經(jīng)詩的吟唱。在這個每天云集著各路行人的大羅盤里,人們似乎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守著規(guī)則,誰也不愿意因破壞了規(guī)則而遭受滅頂之災(zāi)。
那時的八廓街完全是一條環(huán)形的商業(yè)街,物品多是手工藏飾品,還有一些小商品,人也是千姿百態(tài),如此狀況已保持了上千年的歷史。
不過1987年底因為遭受了一小撮人的暴亂,八廓街立馬有些冷清。值錢的店鋪都關(guān)了門,其他小店都是雜貨或飾品,而那時我急需買一個洗衣服用的塑料桶,跑遍拉薩市區(qū)幾家百貨店,愣是沒有買到,最后,只好從八廓街里找了一個打鐵的藏漢,他給我手工打了一個鐵桶,當(dāng)時拎著它回去,真還費了點力氣,畢竟是海拔3750米的高原呀。
那時,拉薩有一位很有名氣的女作家馬麗華,在我非常唐突地登門拜訪時,她絲毫沒有對陌生人有疑慮態(tài)度。我找到她住的小屋,她很客氣地迎我進去,感覺一點不像我想像的名人和作家,說起話來有山東口音,有點像沂蒙山里的軍嫂,看著就是個厚道人。那時她已經(jīng)在西藏待了12年,她說,在西藏是完成自己人生情感和認識的一個很重要的過程,她追求一種真正的生命質(zhì)量,而不是僅限于活著。她跑了西藏許多地方,對大自然和當(dāng)?shù)厝说纳娣绞接幸环N發(fā)自內(nèi)心的興趣,這種愉悅的情緒使她不得不拿起筆表達,向人們訴說……看著她全身散發(fā)的飽滿熱情,很受感染。那個時候的我,別提多么羨慕她這種狀態(tài)了。
她送給我一本剛出版的詩集:《我的太陽》,其中收錄了她1984年所寫的《思念》,我很喜歡。她像我前行的一面鏡子,如今我早已擠進了紛繁的大世界里,周旋在非洲各種酋長屋檐下,27年過去了,我依然記得她詩集里的一段話:“愛到無限,思念到無限,也苦到無限;無窮的苦思,只為一個你?!?
馬麗華作品不計其數(shù),《追你到高原》、《藏北游歷》、《靈魂像風(fēng)》,《走過西藏》等等。她的《藏北游歷》絕對暢銷了很多年。她還曾經(jīng)獲得過老舍文學(xué)獎??墒俏抑辉?988年她的小屋見過她一次,算是一面之交吧。
八十年代在拉薩,人與人之間相當(dāng)簡單,相識或不相識無妨,登門就是客,留客吃飯,喝酒,暢談,再自然不過了。酒足飯飽后,大家會騎著自行車,吼著“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”,各自騎回自己的小窩。那時沒有呼機、手機,想約酒了,飯點前揣瓶小酒,車子騎得比“打飛的”還快,直奔喜歡動手做飯的朋友家,不一會工夫,三兩個硬菜整出來就開喝。經(jīng)常是一頓晚飯,從七點到十二點,陸陸續(xù)續(xù)會有上門討酒討飯的,往往這種人,來得晚,醉得快。有時我也喝成爛泥,當(dāng)即躺倒就睡,大家尋的就是一個開心。
八十年代,每天清晨拉薩城上空飄散著濃郁的香火,從軍區(qū)大門出來,順著金珠路向西走,每隔三四十米,就是一個瑪尼堆,接連不斷的民眾手持轉(zhuǎn)經(jīng)筒,邊唱誦,邊行走,還有小狗陪伴,在晨光下飄渺的香火里,一個又一個時隱時現(xiàn)的身影,為這座城市留下了不同的人文景觀。
我那時有一個小皮箱,夾在自行車的后架子上,里面裝著相機,把車騎到“有感覺”的地方,放下車子,拿起相機拍攝,車子基本不鎖,也很少遭遇拒絕照相的信徒。有時我會緊跟著一個人一路拍下去,他們大都是旁若無人地做自己的事,更談不上辱罵、砸相機之類的舉動。有時遇見漢語說得比較流利的人,還會停下腳步,聊上一會兒。
那時在拉薩城里,普通人的交通工具以自行車或人力三輪車為主,乘公交車的大部分是從城外來的人,由于車少,每個公交車站的馬路牙子上,都會坐著一排候車的人,沒人焦急,也聽不到抱怨,很多公交車,二十分鐘或半個小時才來一趟。
人力三輪車很便宜,基本也就兩三元錢去一個地方,那時的拉薩市,除了大昭寺門前,要數(shù)大菜市場人氣最旺了,賣菜的基本都是四川口音,有時我去那里也會撇上幾句川話,想套個近乎避免缺斤短兩的。
當(dāng)時很少有游客,多數(shù)都是從內(nèi)地去援藏或在那兒工作的人。相比他們,我在軍區(qū)的條件挺牛掰,1、政治部有一個太陽能洗澡堂,2、軍區(qū)禮堂每周放一部電影,3、從后勤部私下能買到內(nèi)地面(通常吃的是當(dāng)?shù)孛妫?、有時還能搞到212吉普車去郊外轉(zhuǎn)轉(zhuǎn)。
不過,掉鏈子的事弄得我好幾次下不來臺。
我曾經(jīng)大冬天的,特?zé)嵝牡亟袔讉€當(dāng)?shù)氐呐笥训秸尾吭杼孟丛?,正趕上太陽能出了問題,洗了一半沒熱水了,把朋友凍得哆嗦著身子出來,那慘樣當(dāng)時差點沒把澡堂子砸了。記得我曾經(jīng)請余華、王文杰等幾個從內(nèi)地去的作家到軍區(qū)禮堂看電影,好不容易擠進去,幾個人都失望得坐不住了,我去……片子已經(jīng)老掉牙了。
人的一生世事難料,打死我也不會想到,在拉薩生活了兩年時間,我居然把自己的婚姻大事解決了——直到如今,看著帶有藏文的結(jié)婚證,我都納悶,我和先生都是北京人,當(dāng)時怎么腦子一熱,在拉薩就把婚給結(jié)了?不是緣分還能是啥。
1999年,離開拉薩十年之后,再次回來,街上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許多餐館,也不再用為買一只塑料桶而奔波,八廓街的商人來自四面八方,他們操著不同的語言,聚居在同一個地方,出租車已經(jīng)取代自行車,歌舞升平的景象怎么看都有北京的影子。
我想,我應(yīng)該與拉薩告別了。
從此開始了我獨自的非洲之旅,一晃15年過去。今天再提起拉薩,顯然那里的一切都無法讓我與當(dāng)年對號入座了,但留在我記憶里的拉薩,誰也搬不走。
我和所有去過拉薩的人一樣,只是一個匆匆的過客。
在我的記憶里只是八十年代的拉薩而已。
大家還在聽